一、韌性與移民
黃仁勳 1963 年出生在台北,九歲時被父母送往美國肯塔基州寄宿。在那個種族意識尚未鬆動的年代,他在寄宿學校裡被同學與老師以「中國佬」稱呼,面對不公義的霸凌,他不只自己應付,還鼓勵朋友一同對抗。
從歐奈達小學畢業時,他已是全校風雲人物。他是班上第一名,在全校集會上獲頒一枚銀幣。他不僅面對辱罵,甚至勇於與其中一位歧視他的老師對抗。當其他孩子還在適應語言與文化衝擊時,他已學會面對敵意,鍛鍊將歧視轉化為一種內在的韌性,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內心的強大。
「那時,人們用『中國佬』這種字眼來稱呼華人。」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
「我們每天都被這樣罵。」
...
「那時沒有輔導人員,」
「沒人會聽你訴苦,你只能堅強起來,繼續前進。」
——《黃仁勳傳》第一章〈橋〉
高三時,他在丹尼餐廳打工。從洗碗工做起,後來升為服務生。當服務生的經驗讓他意識到什麼叫真正的壓力,尖峰時段的餐廳,就像小型戰場。同時他也透過在丹尼餐廳當服務生快速熟悉了美式文化,他幾乎把整份菜單吃了一輪,最愛的是大鳥總匯三明治。對一個移民來說,能在這樣的美式餐廳大快朵頤,油香、鹹脆、熱騰騰的三明治,大概是當時最具「美國感」的日常時刻了。
「我發現在逆境時我的頭腦最靈光。這個世界崩塌時,我的心跳反而變慢。」
「也許這源於我在丹尼餐廳的歷練。當服務生就得面對尖峰時刻的考驗,恨不得自己有三頭六臂。任何應付過餐廳尖峰時段的人都明白我的意思。」
——《黃仁勳傳》第一章〈橋〉
二、黃仁勳的性格,紀律與冒險
讀《黃仁勳傳》的時候,我腦海裡浮現的是兩種性格的巧妙組合:一邊是台灣竹科式的認真和紀律、一邊是矽谷創業者的冒險精神。他極度嚴格又極度真誠,習慣高壓驅動團隊,又願意停下腳步親自詢問基層實際的工作情況。
黃仁勳覺得絕境才是勝利之母,這是他在公司創辦初期開發 NV1 至 NV3 最真實的公司經營經驗。「我們公司再三十天就要倒閉了」是黃仁勳在關鍵時刻反覆提醒團隊的一句話。直到今天,這句話仍掛在輝達文化的牆上。他最常談到幾個相同主題: 以「光速排程法」進行調度的重要性;追求傳說中的「零億美元市場」;以及最重要的,提醒員工科層體制的危險永遠潛伏在一旁。
黃仁勳習慣以「第一性原理」思考問題。當他第一次意識到深度學習的潛力,他會清空週末行程,一口氣讀完相關本書,再回頭與工程主管討論。這種強迫症式的學習方式,讓他能在關鍵時刻下出讓人驚訝後來卻證明正確的決定。
2012 年,黃仁勳賭上全公司資源轉向 AI。黃仁勳當時下了一個結論,認為神經網路必將給社會帶來革命性的轉變,而他也將能壟斷 AI 必要的硬體市場。 他曾在一次週五深夜寄出信件,宣布NVIDIA 將全力投入深度學習;到了下週一早上,公司已經變成一家AI公司,他對邏輯與未來有絕對的信心。
黃仁勳超乎常人的專注認真,也不怕賭一把;他能把市場行銷書一口氣看完,也能在會議桌上用工程邏輯力壓一整個產品團隊。這造就了 NVIDIA 公司裡面的文化與調性,幾乎就是創辦人性格的複製體。
三、關鍵交會:CUDA 平行運算與 AI 時代
NVIDIA 能在這波 AI 浪潮中站上浪頭,靠的是兩項關鍵技術的交會:一是以 CUDA 為核心的平行運算架構,二是生成式 AI 帶來的寒武紀式的大爆發。
在平行運算領域 CUDA 是 NVIDIA 築起運算護城河的關鍵軟體。它的全名是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,中文是「統一運算架構」。把本來用來跑遊戲畫面的 GPU,變成能處理科學與資料計算的通用平台。
對多數工程師來說,CUDA 一開始是個難學又難用的開發工具,在輝達內部也曾被質疑過。但黃仁勳在這邊賭了一把,他不只對內力挺,也積極尋求外部合作。他親自拜訪台灣大學物理系的趙挺偉教授,請對方協助驗證 GPU 在學術計算上的可行性,並逐步把這項潛力轉化為實際研究成果。
「黃仁勳是個有遠見的人,」趙教授說,「因為他,我這一生的研究才得以從理論變成現實。」
——《黃仁勳傳》第十章〈共振〉
在 AI 的歷史上,AlexNet 是史上第一個成功用 GPU 訓練深度神經網路的案例。它不是在研究中心的超級電腦上誕生,而是在克里澤夫斯基的臥室裡、用一張 GeForce GTX 580 執行完成的。這種「非正規軍」的開發風格,後來反而成為 NVIDIA 的戰略制度:賦能開發者、提供工具、打造平台,彷彿一間軍火工廠,讓每一個 AI 創業者都能從這裡獲取火力。
隨著 Transformer 架構問世,再加上大規模平行運算日趨成熟,生成式 AI 在 2022 年迎來了真正的寒武紀式爆發。ChatGPT、Midjourney、Copilot、AlphaFold...... 幾乎每一項顛覆性的突破背後,都有 NVIDIA 的計算能力支撐。
「AI 領域的戰爭開打,而輝達是唯一的軍火商。」
——《黃仁勳傳》第十七章〈錢〉
NVIDIA CEO Jen-Hsun Huang and OpenAI Co-Founder Elon Musk with the first DGX-1
四、結語:創新者的兩難
最後值得一提的是,黃仁勳要求他的管理團隊讀《創新者的兩難》,甚至邀請作者克里斯汀生擔任顧問。
《創新者的兩難》奧妙的地方在於「如何避免錯過未來」。
破壞性技術往往不是從主流機構誕生,而是從邊陲、愛好者社群中開始發芽。他們用現成的組件拼出新用途,初期功能粗糙,但因為無人關注,反而有空間快速演化。
即使領悟這個道理,實行起來也並不容易。追求小眾市場會犧牲獲利,投資人會質疑你的判斷,克里斯汀生說:「老牌公司的管理者難以切入新興市場的原因之一就是,投資人與客戶都告訴他們不要這麽做。」
黃仁勳與 NVIDIA 的發展經驗,可被視為《創新者的兩難》理論的一個具體案例。正是黃仁勳的眼光和堅持,持續押注破壞性技術,最終讓公司成為價值數億美元超級電腦供應商,成為科技產業的霸主。
References
黃仁勳傳:輝達創辦人如何打造全球最搶手的晶片
The Thinking Machine: Jensen Huang, Nvidia, and the World’s Most Coveted Microchip
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1010307
Wiki - 黃仁勳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9%BB%83%E4%BB%81%E5%8B%B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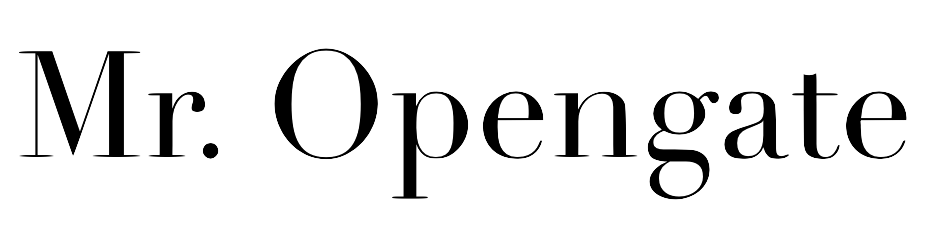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